如何理解天氣和氣候的關系?“南旱北澇”是否會成為未來趨勢?
今年“十一”長假,本該秋高氣爽的華北地區陰雨連綿,而長江以南卻經歷了史上最“暖”的國慶檔,還沒等緩過神來,10月中旬的一輪大范圍寒潮倏忽而至,全國各地網友都大呼反常。
不僅人們感知到的天氣不太尋常,數據統計更能說明問題。歷數今年過去的約300天,全國范圍內一項項天氣紀錄被打破:全國平均氣溫創196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3月14-15日,京津冀晉等12省市出現近10年來范圍最大、強度最強的沙塵天氣;鄭州最大小時降雨量達201.9毫米,突破我國大陸小時降雨量歷史極值……
這一年,極端天氣罕見地頻繁“打擾”著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另外一些人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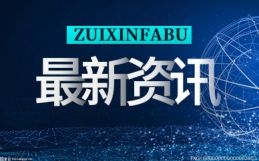
如果要用一個關鍵詞來總結今年的異常天氣,“南旱北澇”取代了人們更為熟悉的“南澇北旱”,究其成因,國家氣候中心專家稱,是由多重因素疊加形成:夏季風環流系統組合式異常是主因;拉尼娜是北方秋汛持續的元兇之一;以及全球變暖加劇了氣候系統的不穩定等。
今年冬天,拉尼娜再度降臨,雖然有可能導致冬季氣溫偏低,但今年是否會是冷冬?考慮到氣候系統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全球已然形成共識,近年來極端天氣的增多增強源于全球變暖。在中國河南暴雨的同一時期,西歐、美國也遭到洪災襲擊。截至10月,美國損失十億美元以上的天氣氣候事件多達18次。在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全世界都處在“命運共同體”。
即使幸免于威脅到人類生命的極端天氣,更有專家指出,“氣候變化是本世紀人類健康的最大威脅。”
10月31日,《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以來的首次氣候大會在英國召開,中國碳中和碳達峰的“雙碳”目標已十分明確,而全球溫升不超過1.5℃的長期目標該如何共同實現?
時間或許是唯一的答案。
秋汛秋雨和“南旱北澇”
今年以來,我國天氣氣候的主要特點,包括降水“北多南少”、南方地區秋老虎明顯、登陸臺風數少但十月頻繁、雙拉尼娜事件對副高等氣候影響十分典型……10月27日,國家氣候中心氣候服務首席專家周兵面對媒體,集中回應了公眾關切的氣象問題。
據國家氣候中心給出的數據,今年以來(以下數據均截止到10月25日),全國平均降水量634.9毫米,較常年同期偏多6.6%。北方地區降水量668.7毫米,歷史同期第二多,僅次于1964年的684.5毫米。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陜西等省(市)降水量均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
于是,那些罕見的場景發生了:南疆極端降雨疊加天山季節性融雪,7月中旬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部遭遇洪水。北京密云水庫蓄水量暴增,在8月底超過了 “歷史最高水位線”。河南、山西、陜西等地意外遭受了極端暴雨導致的洪澇災害。
而在我國南方,今年夏秋被持續的高溫所籠罩著。今年以來,全國平均高溫日數(指日高溫達到或超過35℃)有12.0天,較常年同期偏多4.3天。9月以來,南方地區平均氣溫達22.7℃,較常年同期偏高1.5℃,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高。高溫少雨致使廣西、湖南部分地區出現旱情,農作物受災甚至絕收。
中國氣象局原副局長許小峰向《等深線》記者分析,今年的降雨分布有比較明顯的異常,副熱帶高壓強盛且北抬,穩定維持,加上來自西北太平洋的東南暖濕氣流和來自印度洋的西南暖濕氣流異常強盛,雨帶在北方維持,受到副熱帶高壓控制的南方地區高溫少雨。
氣象學上所稱的副熱帶,即一般地理上所說的亞熱帶。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西北太平洋上的高壓中心,也稱西北太平洋副高。
“副高是造成我國夏季旱澇變化的主要天氣系統之一。”國家氣候中心氣候預測室首席高輝曾這樣解讀,西北太平洋副高對我國天氣的影響十分明顯,夏季尤為突出,“我國酷暑的持續、雨帶的變化、臺風的活動等,大都與副高直接相關。”
冬季到夏季,隨著太陽直射點從南向北移動,副高有規律地自南向北推移。從夏到冬,副高再有規律地自北向南撤退。
可以這樣講,一定程度上,西太平洋副高的南北位置決定了中國的雨季進程,而今年,副高顯然“不按常理出牌”,直接跳到了我國東北至太平洋西北部的日本海一帶,遠遠超出常年一般只到黃河流域的范圍。
以河南暴雨為例,中央氣象臺回應稱,西北太平洋副高位置相對偏北,和臺風“煙花”之間形成了穩定偏東氣流,給河南地區持續輸送水汽。并且由于副高位置的異常,河南正處于副高邊緣地帶,對流明顯,短時強降雨特征明顯。
“我國是一個受季風性氣候影響極為顯著的國家,所以在進行極端天氣事件解讀的過程當中,腦海里永遠要裝著中國雨季進程的一個概念。”周兵說。
隨著副高移動的位置南北往復,我國南北方通常會先后形成華南前汛期、西南雨季、梅雨雨季、東北雨季、華北雨季和華西秋雨。
詩人李商隱的名句“巴山夜雨漲秋池”正是描繪華西秋雨的景象。“今年由于副熱帶高壓位置的偏北,使得華西秋雨強度增強,華北到東北西部等地的降水明顯增多。”周兵表示。
周兵分析稱,秋汛秋雨與“南旱北澇”的成因也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全球變暖加劇了氣候系統的不穩定和水循環,使得大氣不穩定增大,降水效率提高,強降水更加顯著”。
北京師范大學減災與應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楊靜認為,河南、山西強降水的成因和全球變暖必然有聯系。她分析稱,以前同樣的一個低壓產生不了這么大的降水。現在,整個大氣里水汽含量增多了,同樣的一個上升運動產生的降水就會增多。
中國天氣網曾梳理出1470年~2018年間我國的旱澇數據,數據顯示,中國旱澇格局呈現周期性變化,其中,最常見的是“南澇北旱”,大約平均每4年就可能出現一次,而“南旱北澇”最為少見,大約平均每九年出現一次,連續2年“北澇南旱”的狀況在歷史上更為少見。
“南旱北澇”是否會成為未來趨勢?
2013年也是一個“南旱北澇”的年份,多位專家就曾對這一話題有過一番爭議。當時有“趨勢說”和“不確定說”兩種觀點。前者認為,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會形成“南旱北澇”的趨勢;而后者堅信,雨帶的變化是長期的過程,不能僅根據一次反常的天氣過程就斷言雨帶或熱中心的轉移。
持有“不確定說”觀點的中國氣象科學院研究員祝從文表示,“氣候預報的難點在于,目前我們仍無法針對特定年份對全年氣候作準確評估。就算未來‘南旱北澇’,也不是單純的‘南方準備抗旱、北方注意防汛’那么簡單。”
“趨勢說”觀點的持有者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計劃首席科學家李維京發現,我國的雨帶有非常顯著的年代變化特征,“未來,隨著全球變暖的持續,我國主雨帶很可能北移”。
周兵介紹,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只有一條主雨帶,主要位于黃河以北地區;1980年開始,主汛期出現了南北兩條雨帶,且這兩條雨帶呈同步變化趨勢,2010年之前兩條雨帶均一致表現出南移的趨勢,2010年之后雨帶又開始出現明顯的北抬北擴。
周兵指出,我國由于受到季風氣候的影響,氣候的特點表現出年際之間變率大,所以年和年之間降水量的差異是非常顯著的,某種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自然變化的規律。
“南旱北澇”可能不會連年發生,但有權威報告預測,未來的總體趨勢是北方降水增多。
2015年11月正式出版的《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預測,到21世紀末,中國將持續降水變多的趨勢。全國降水平均增幅為2%-5%,北方降水可能增加5%-15%,華南地區降水變化不顯著。
雙拉尼娜年
氣象的變幻總是與多個天氣系統相互關聯,環環相扣。
“大氣的記憶力較差。”許小峰形容道,大氣的變化很快,每天的溫度、氣壓、降雨都在不斷變化,而海溫的穩定性較強,海溫異常時會引起上方大氣環流的變化。
拉尼娜是西班牙語“La Niña”的音譯,原意為小女孩,和小男孩厄爾尼諾(El Niño)現象相對立。拉尼娜是指赤道中、東太平洋海表溫度與常年同期相比出現大范圍偏冷,且強度和持續時間達到一定條件的現象。
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就發生了拉尼娜事件。拉尼娜的形成,一般會造成中國降水分布呈現北多、南少型,氣溫分布則為冷冬、熱夏型。
今年以來,北方地區降水量為歷史同期第二多,唯一超越今年的是1964年,當年也是一個拉尼娜年。“自然而然我們把這種降水的異常,尤其是秋季以來降水的異常跟拉尼娜掛上勾。”周兵說。
周兵介紹,拉尼娜的出現,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可預報性,一般的周期是2年~7年,平均周期為4年。
據國家氣候中心10月22日最新消息,今年7月以來,赤道中東太平洋海溫持續下降,預計10月進入拉尼娜狀態,并于冬季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強度的拉尼娜事件。
鑒于2020/2021年冬季已經發生了拉尼娜,今年將形成“雙峰型拉尼娜”。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季風系統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提示稱,連續兩年冬天出現拉尼娜事件其實并不鮮見。上一次出現是在2010/11年和2011/12年的冬天。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拉尼娜事件與冷冬并不能直接劃上等號。
從歷史數據來看,拉尼娜年我國冬季中東部地區氣溫往往偏低。不算今年,1950年以來,全球共發生了15次拉尼娜事件,有10個冬天偏冷、5個偏暖,僅出現過1次強拉尼娜事件,有9次中等強度事件;其他均為弱事件。2008年1月席卷中國南方的雪災,就與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的一次中等強度的拉尼娜現象有關。
而上一年冬天整體表現為前冬冷后冬暖。2021年3月3日,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官宣確定2020/21年冬季為暖冬,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溫度達到暖冬標準。據了解,判定冷暖冬的基本要素為冬季(12月至次年2月)三個月的平均氣溫,在空間上分為單站、區域、全國三個范圍等級。
魏科撰文表示,影響我國冬季氣候異常的因子非常多,僅用拉尼娜一點來討論氣候,容易“以偏概全”。影響因子不僅包括熱帶中東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以及我國近海的海溫狀況;還包括中高緯北極海冰、歐亞雪蓋和陸面狀況等,“各個區域不同影響因子的作用有所不同,各區域的權重并不相同”。
而知名氣象科普博主“中國氣象愛好者”認為,在典型、雙峰拉尼娜和NPMM-背景下的這個冬天,偏冷可能性正在加大。其撰文寫道,海溫監測顯示,此次拉尼娜的冷水區域,比前一次更偏西些,更接近歷史上典型的拉尼娜年。典型的拉尼娜,更加容易導致我國中東部冬季偏冷。
中國氣象愛好者梳理數據發現,我國冬季的冷暖與副熱帶北太平洋經向模(NPMM)的位相有關。目前,北太平洋NPMM轉為負位相,按照1950年以來的數據推斷,當拉尼娜發生,且NPMM為負位相時,我國冬季總體偏冷。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變暖加持下,這個冬天不太可能是規規矩矩的冷,而是上躥下跳的一會兒特別暖,一會兒特別冷,回暖和降溫都可能有極端性。對此,我們需要有心理準備。”中國氣象愛好者稱。
極端天氣與氣候變化
如何理解天氣和氣候的關系?周兵解釋稱,天氣是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氣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段時間里的天氣的統計特點。
我們常常講極端天氣,到底什么是極端天氣?
許小峰說,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遇到比較罕見的天氣基本上就可以稱之為極端。
周兵給出專業領域中量化的定義,一般把某種天氣或氣候變量值出現概率低于10%的現象稱為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并且,某些氣候極值或事件不一定是單次發生的,可以是多次天氣或氣候事件積累的結果。
許小峰告訴記者,極端天氣,特別是尺度比較大、大家感受強烈的極端天氣,都不會只發生在一個地方,就像蹺蹺板,一個地方的氣壓低了,或者溫度低了,另外的地方就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今年以來全球范圍內極端天氣的多發頻發。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嚴中偉向記者指出,即使沒有全球變暖,各地也會發生熱浪、暴雨等極端天氣和偏冷、偏旱等氣候異常,這屬于“氣候變率”的范疇。然而,全球變暖會影響各地的氣候變率。比如,某些區域過去“十年一遇”的極端熱浪正在變成幾乎每年遭遇的“常態”。
對于氣候問題,許小峰談到一個人們極易產生的誤區,許多人將大氣短期的變化,如一年的降雨變化或氣溫波動上升到氣候變化的高度。他強調,“天氣變化和氣候變化不一樣,氣候問題是一個長時期的積累。”
2021年8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發布了第六次氣候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以下簡稱“IPCC報告”),共有來自66個國家的234位作者參與撰寫,其中來自中國的有15位。
IPCC報告主要作者中國科學院周天軍、浙江大學曹龍撰文總結稱,科學界在一些關鍵結論上形成共識,其中包括,近期的氣候變化是廣泛、快速和不斷加強的,觀測到的許多變化在過去數千年間前所未有;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人為影響正在導致包括熱浪、強降水和干旱在內的極端天氣事件變得更為頻繁和嚴重。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1)》指出,1961年-2020年,中國極端高溫和強降水事件呈現增多趨勢。而在城市熱島、雨島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城區的高溫和極端降水出現的頻率和強度高于周邊地區。
中國又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影響顯著區,升溫速率明顯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塵總結稱,氣候變化對我國糧食、水資源、生態環境、能源、重大工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等諸多領域帶來嚴峻挑戰,氣候風險水平進一步升高。
最直觀的后果是經濟損失。巢清塵給出的一組數據顯示,極端天氣氣候災害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由1984年-2000年的平均每年1208億元增加到2000年-2019年的平均每年2908億元,增加了1.4倍。
氣候變化與健康
東京奧運會期間,當地經歷了高溫、潮濕的天氣。2021年8月5日中午,東京的氣溫達34℃,在濕度64%的情況下,體感溫度接近43℃。有運動員因高溫暈倒,被擔架抬離現場,或因中暑中途退賽,坐輪椅離開賽場 。
“氣候變化是本世紀人類健康最大威脅”。柳葉刀倒計時亞洲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副教授蔡聞佳向記者解釋道,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響存在于方方面面。熱浪天氣對老人、兒童和孕婦等脆弱人群,都有較為直接的影響,會增加人群的死亡率和發病率,通常是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加重,而引起的過早死亡。
據《柳葉刀倒計時2020年中國報告》(以下簡稱“柳葉刀倒計時報告”),中國受到的氣候變化影響主要表現為,氣溫升高、極端天氣事件增加和媒介生態改變造成的健康危害。在過去20年,熱浪相關死亡人數上升了4倍,2019年的死亡人數達到2.68萬人。
黃存瑞是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氣候變化與健康方向的研究。他解釋道,山東歸因于熱浪相關死亡人數最多,與當地的人口數量、老年人口比例以及對健康影響的暴露反應有關。南方居民的適應性更強,包括生理的適應性、建筑設計、對空調的使用等,反而相對風險會更低。
黃存瑞表示,科學界在過去十年中對氣候變化健康影響的關注度在逐漸提升。不僅關注空氣污染和極端溫度的健康影響,還關注糧食安全,例如,溫室氣體濃度增加,會導致一些農作物營養成分下降;干旱或洪澇等氣候災害造成糧食絕收,影響農民生計,對其精神心理健康產生危害;以及由于全球變暖造成的蚊蟲等病媒生物地理分布范圍會擴大;土壤、水質也會發生變化等。
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森林火災等的增加,以及氣候敏感性疾病的傳播與流行,將進一步造成嚴重的健康影響。據柳葉刀倒計時報告,登革熱是一種典型的氣候敏感性媒介傳染病,其氣候適宜性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上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通過埃及伊蚊和白紋伊蚊傳播登革熱的媒介能量分別提高了37%和14%。
“中國暴發的登革熱疫情,現已不僅僅局限在廣東、云南這些地區,也擴散到山東、河南等北方省份。”黃存瑞說,原來北方冬天很冷,蚊子難以過冬,現在由于全球變暖,很多病媒生物的地理分布都在向北擴散。
“世衛組織在2014年有一個估計,大約每年有25萬人的死亡與氣候變化有關。”蔡聞佳說,由于這只是一個保守估計,而同時全球氣候變化的趨勢仍在繼續,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死亡人數預計仍會持續增加下去。
1.5℃
將全球氣溫上升整體控制在相對于工業化前不超過2℃,且每十年溫升不超過0.1℃,由上世紀八九年代的歐洲學者首先提出,他們認為這是地球容忍的上線。此后,眾多氣候變化會議都強調了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2009年,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上,一些島嶼國家提出1.5℃的溫升也足以威脅到他們的生存。之后,一些欠發達國家也加入進來,堅持將長期氣候目標定為全球溫升不超過1.5℃。
2015年,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黎協定》,把“相對于工業化前的全球平均溫升水平控制在2℃以內,并努力爭取控制在 1.5℃以內” 寫入協定。
無論是2℃還是1.5℃,看上去都不是一個多么可怕的數字,可全球氣溫每上升1℃,大氣水汽增加約7%,從而導致極端降水增加,還會有更多地區遭遇更頻繁更嚴重的干旱,絕大部分人類居住的地方都將出現更多、更強、更持久的極端高溫。
頗為嚴峻的是,目前的溫升水平距1.5℃的目標并不遙遠。IPCC報告顯示,2011年-202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溫度比1850年-1900年升高1.09℃。
溫升過快的后果不堪設想。就高溫而言,IPCC報告稱,1850年-1900年間平均50年才發生1次的極端高溫事件,在當前氣候狀態下大約每10年發生1次;如果實現了1.5℃的溫控目標,大約每5年發生1次;而若放任全球升溫至4℃,則每年都會遭遇至少1次同等嚴重的高溫。
IPCC報告對未來全球的氣溫進行了預估,并給出了五種預估情境,分別對應了從極低到極高排放的五條路徑。即使是極低排放的情況,在本世紀30年代全球溫升也將達到并超過1.5℃。
周天軍、曹龍認為,如果快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在2050年前后實現二氧化碳凈零排放,那么到本世紀末,非常可能的是全球平均溫升幅度有望被控制在2ºC以內;多半可能的是,全球平均溫升幅度將低于1.6ºC、并且在本世紀末減少到1.5ºC。這也將仰賴于各國的減排行動。
“雙碳”前景
“任何一個地方的氣候變化,一定是人類活動和自然變率共同影響的結果。”楊靜解釋稱,這就是為什么在2000年-2010年的10年間突然出現了“全球變暖停滯”現象,并不是說那段時間不排放二氧化碳了,而是那10年剛好出現了一個冷異常的自然變率擾動的位相,然后跟二氧化碳增長的位相抵消了。
楊靜將排除人類活動之外自然因素引起的波動比作一個彈簧振子——“彈過去到頭,它會再回來”,但是人類的這種二氧化碳排放常常是沒有閾值的,“溫度就一直在增暖,不會回頭”。
“如果排放不停止的話,它還會到達自然可控的一些閾值,但可能是比較危險的。”楊靜強調。
截至2021年7月底,全球共70個國家提出了到2050年左右實現氣候中和、碳中和、溫室氣體中和或凈零排放的長期減緩的愿景和目標。
碳中和,是指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巢清塵介紹,《巴黎協定》中有一個關于全球盤點的規則,即為解決各國“自主貢獻”力度不足以實現溫控目標等問題,從2023年開始,每5年將有一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盤點,以幫助各國提高行動力度。
我國碳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的28%,與發達國家相比,實現碳中和面臨更大的挑戰。
“歐美各國經濟發展成熟,已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絕對脫鉤。”巢清塵表示,而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發展的能源需求不斷增加,碳排放尚未達峰。要統籌協調社會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轉型、能源低碳轉型以及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難度很大。
10月24日-26日,國務院先后印發被視作“雙碳”頂層設計文件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及《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方案》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順利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碳中和目標順利實現。在能源結構上,《方案》提出要推進煤炭替代和轉型升級。
“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從目前化石能源占比15.9%,逐步過渡到206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比80%,一定是個艱巨的過程。”巢清塵說,必須要有節奏逐步轉型,不能犧牲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未來即使達到碳中和,也不意味著煤炭完全退出,仍需要充當“備胎”作用,作為清潔能源的調峰替代。
應對極端天氣
如果按照IPCC預估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全球溫升達到1.5℃已是一種必然,這也意味著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一系列極端天氣事件將變得更為頻繁和嚴重。氣候韌性城市的建設必不可少,并且被專家稱為“是解決眼前問題的措施”。
今年的幾次極端天氣事件讓蔡聞佳意識到,加強韌性城市的建設刻不容緩。“城市里的許多基礎設施在面對極端天氣時比較脆弱,交通運輸樞紐,會因極端天氣中斷,地鐵、私家車會因內澇而無法出行,醫院的正常運行會受影響,醫療設備受到損壞。”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李國慶在《韌性城市的建設理念與實踐路徑》中寫道,韌性城市的概念在中國首先被應用于城市氣候風險領域,被視為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城市調適模式。一方面,當前氣候風險對當今城市威脅顯著。另一方面,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3%,9億多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與城市群,急需提升城市韌性水平,強化城市抵御風險能力和災后恢復能力。
早在2017年,國家層面已有所行動。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氣候適應型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呼和浩特、大連等28個城市被列為試點名單。
巢清塵曾參加過一些城市適應氣候變化的工作,她常常發現很多城市并未詳細開展過氣候風險評估工作,“不能清晰了解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和未來面臨的風險情況,就難以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完善和改造。未來氣候變化將帶來更多更強的極端事件,必須及早關注”。
蔡聞佳提出,城市的很多部門在應急管理上,沒有把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可能還以曾經的經驗提出應急管理方案。她認為,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需要警惕升級的風險和新增的風險,例如,2020年有多個臺風深入襲擊東北,可謂前所未見。
據許小峰了解,氣象部門、各級政府、各企業都制定了針對極端天氣的應急預案,然而,在氣象部門作為“第一道防線”發出預警信號后,部門之間相互的銜接、預案的落實都有待提高,而且預案是不是能夠符合實際,需要經過實際檢驗,有問題的要及時調整。“我印象中在2005年前后,國家開始制定各項應急預案,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有些事情沒有發生,雖然有預案,但沒有經過經常的演練,沒有經過實踐,就變成紙上談兵了。所以預案一方面要制定,另外要真正地有一個實踐的過程,或者至少有個演練的過程,你才能知道會產生什么情況。”許小峰建議。
談及如何更好地提供氣象服務的保障,以應對極端天氣多發的挑戰。周兵表示,氣象部門將切實做好精密監測、精準預測、精細服務。
“極端天氣的發生往往超出氣象預報服務人員對以往規律的認知,數值模式對其預報的能力也有限,加大了精準預報的難度。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提前發布的預報預警在極端天氣發生的強度、影響的范圍、出現的時段上尚存偏差;氣象部門采取滾動訂正預報、遞進式服務可適當彌補了上述短板,但與政府需求和公眾期望仍有差距。”周兵說。
他期待,氣象部門跟社會共同推進預警的落地,比如針對不同的行業設置不同的預警,采取相應的措施,“預警要走上一個規范化或者法制化的一個進程”。
在巢清塵看來,高度統一集中權威的組織領導是防災減災的一個重要機制保障。放眼國際,發達國家的風險轉移機制值得我國借鑒。
巢清塵透露,我國正在建立巨災保險制度,重點針對農業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城鄉居民住宅地震保險等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她提到,天氣指數農業保險是一種新型特色農險,是指投保人投保的種植物或養殖物因天氣異常遭受經濟損失后,由保險公司按照約定的天氣指數賠償條件向投保人提供賠償的保險產品。
“通過金融手段降低風險,是發達國家普遍實施的一種市場化手段,這方面我國仍需不斷加強。”巢清塵說。
(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萬笑天 張錦 北京報道)
- 如何理解天氣和氣候的關系?“南旱北澇”是否會成為未來趨勢?
- 兒童發熱怎么辦?家長需要注意什么?
- 膽囊結石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預防?
- 在發生肝癌之前 身體會給我們哪些提示?這些癥狀你要知道
- “眼中風”致盲率高達80% 會導致失明!
- “老年人模式”下的手機實際使用效果如何呢?
- 分餐制:將公筷公勺成為健康“新食尚”
- “雙減”之下 學校體育該如何發力?
- 不斷完善中西醫結合各項制度 為中醫藥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 中老年奶粉代表性單品缺乏 形成差異化競爭趨勢
- 成立“江西綠色生態”品牌促進會 加速推進綠色生態產業鏈建設
- 脂肪肝就是肝臟里囤的“油”多了點 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 喝水有哪些重要性?什么時候喝水最好?
- 養生之道:“小動作 大能量”
- 2021年全國食品安全標準與風險監測評估工作會在京召開
- 頻繁攝入碳酸飲料會產生睡眠障礙
- 保健品可以排毒 減肥 治便秘?是真的嗎?
- 心臟疾病主要有哪幾種?怎么預防?
- 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術前減重是必要的有效治療
- 創新教醫結合模式 做好健康科普智慧傳播
最新資訊
